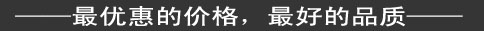为了“味道”,公司三次请来市上党梆子名家张保平、郭孝明、卢爱琴等人,对戏中的“唱念做打”细细往过抠;还把临汾蒲剧团的大腕请到演出现场,进行唱腔、音乐或舞台指导。唱了30多年戏的樊花琴感触深刻:许多演员原来只注重表面化的东西,缺少深层次的挖掘,经过名家指点,觉得受益匪浅。
如果你想独领风骚,就要有承受挫折的能力和不服输的倔劲。公司成立头一个月,他们紧锣密鼓开始排练蒲剧《武士敏》,并参加了市里组织的第十一届“凤鸣春晓”赵树理戏剧优秀剧目展演。尽管这次比赛他们垫了底,精品意识却在他们心中深深扎下了根;尽管他们的水平与兄弟县(市)比有一些差距,但心里憋着一股劲:明年再决高下。
犹如东风般的政策把十几年缠在50多人心头的忧愁顷刻之间消除了,他们眉开眼笑,期待着美好未来。
他们缴纳不起医疗、社保等保险,十分担忧将来靠什么养老。三年前,团里就有个职工到了退休年龄,可无法办理退休手续,去哪领社保金没着落;职工病了,没地方报销;近20年换了8任团长,工作就是没起色。有人拍桌子、摔杯子:“吃‘皇粮’的没饭吃,有事业身份的又显不出价值,这叫什么事呀?”
今年2月6日晚,他们相约而至,参演的现代戏《儿行千里》先后赢得观众九次雷鸣般的掌声。“沁水是进步最快的一个团。”郭孝明等评委这样肯定:是体制改革让沁水剧团打了翻身仗!
55岁的李志进,腿患有骨膜炎,走路有些跛,有时上厕所还得自带小板凳,以起立时当扶手。可在舞台上,根本看不出他的“毛病”。别人担心,他总说“不碍事”。他说,舞台是他衣食住行的保障,也是他人生的归宿。

没有市场就没有收入。表面上看,他们是事业单位,可工资、福利全靠自己挣。其收入只有演出费和县政府“送戏下乡”的补贴,就连主演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也只有1800元,一般演员仅有几百元,下个月还能不能领这么多心里没底。
剧团改革不是“甩包袱”,更不是“断粮”,最大目的就是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,激发文艺团体的创新活力,弘扬主旋律,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,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。
如果你想奋起直追,浑身都是澎湃的力量。公司成立第六天,就带着《金狮坠》等看家节目外出演戏。这一年,他们风餐露宿,不畏艰辛,行程万余公里,走进长治、晋城、临汾等地的67个乡村,播下了诚实守信、技艺精湛的种子。
改制前的蒲剧团和上党梆子剧团是什么样的状况呢?
沁水县上党梆子剧团除了和蒲剧团一样的遭遇外,生存状况更差,能调走的调走了,能跳槽的跳槽了,50多人的单位最后就剩14个,瘫痪了十几年。
□图/文 本报记者 李斌
沁水县以前有两个县管剧团:蒲剧团和上党梆子剧团,近20年来始终处于低迷状态,两个剧团一年演出五六十场,收入不到几十万元,工资没保障,养老、医疗、工伤保险缴不起,资产除办公楼和演出道具外,几乎为零。
把市场需求变成长盛不衰的生命力
蒲剧团曾有过辉煌,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开始走下坡路。“一年52个星期,我们能有52场演出就不错了。”曾经当过团长的杨伟民说,沁水一个团都吃不饱,更别说两个团了。他和许多演员认为,沁水地大人稀市场小,是剧团低迷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公司当家人是43岁的杨赵军,以前是该县上党梆子剧团的演员,后来经商,近几年还经常给晋城、长治等地的剧团拉演出业务。
樊花琴原来留着一头披肩秀发,为了符合《儿行千里》剧中“母亲”的形象,一狠心剪掉了长发;为了演得像“母亲”,演出演出策划多元化公司,她回到乡下一住就是七八天,给婆婆当“学生”,模仿婆婆的言谈举止或情绪变化;
这一年,这家公司共演出460多场,总收入200多万元,职工人均收入破3万元,与改制前的2015年相比,分别增长了32%、21%和57%,同时,还给职工们足额缴纳了养老和医疗等保险。

 手机直线:15054116080
手机直线:15054116080
 在线客服
在线客服